
红星书评|诗人作家争鸣马平长篇小说《塞影记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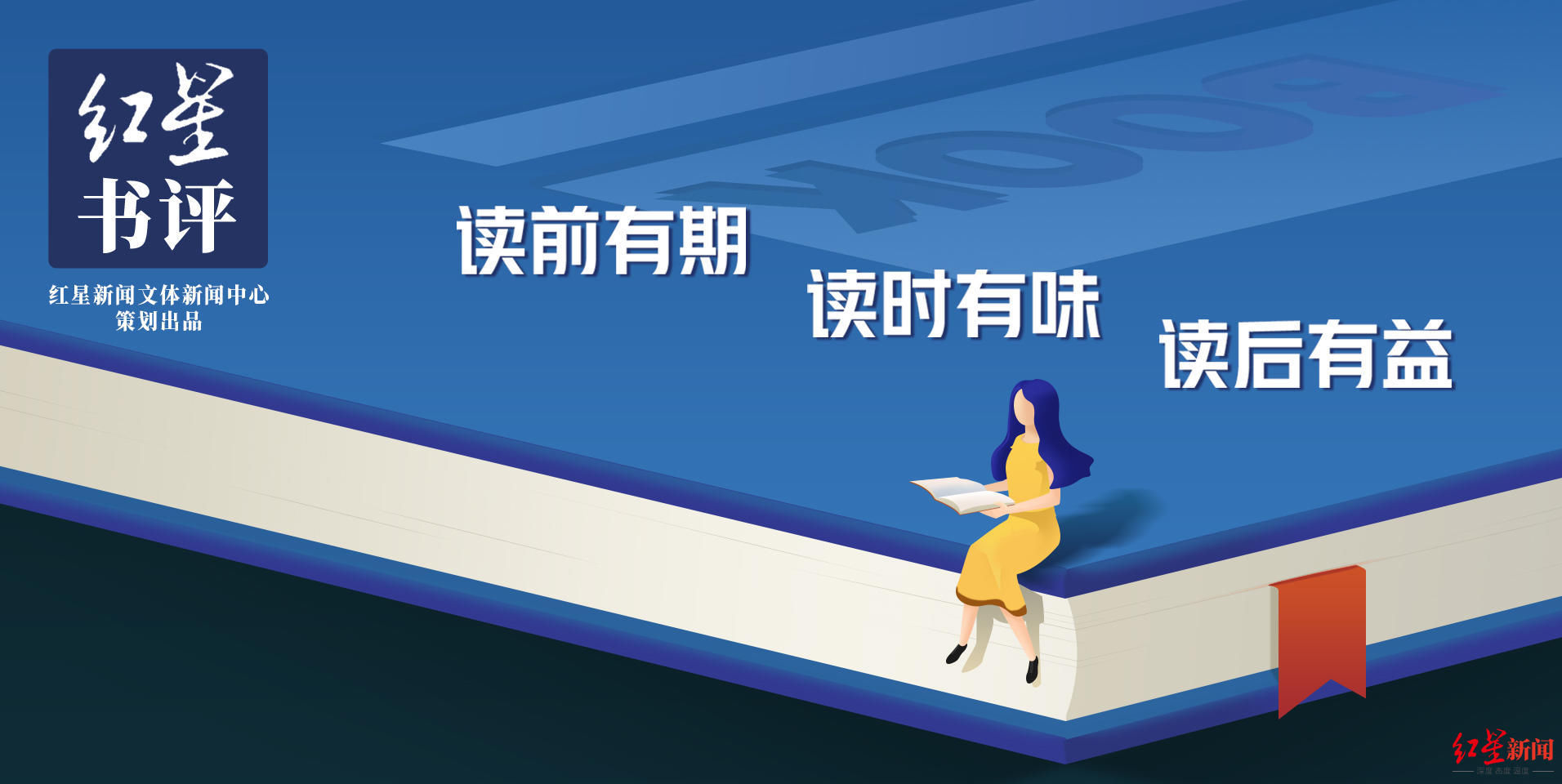
编者按:
马平的长篇小说《塞影记》出版之后,出现了一个热门现象:作家评论家纷纷加入你争我论的评论阵容。今日,红星新闻文化频道《红星书评》,特别推出作家龚莹莹和诗人孙建军的书评,以飨《塞影记》读者。
·作家之眼·
空间和语言承载的文学理想
——读马平长篇小说《塞影记》
◎ 龚莹莹(作家)
小说《塞影记》以简单的故事和诗性的语言受到评论家称赞,作家蒋蓝就将作者马平定义为诗人小说家。语言的诗性曾被法国评论家莫里斯·布朗肖称为是“一种自沉默寂静中升起的若有若无的低语”,《塞影记》也在寂静而虚无中等待,“等穷追不舍的读者”将它唤醒,重生。本文将从空间和语言两个维度探索该作品反映的文学理想。
地域写作的超越与文学写作的暗道
《塞影记》的故事发生在中国四川的北部乡村,地域通常会决定书写的历史传统、风俗人情、生活习惯和审美取向。在李劼人、郭沫若、巴金、马识途等前辈的著作中,巴蜀地域的当代写作已经登峰造极。地域为文学写作提供着力点,同时也是困境,一味深耕难免掘井成蛙,灵感枯竭。小说中多有涉及,也提到“撞车”,“撞车最多的,还是写戏班那些戏,你抄我,我抄你。”故事的地理位置似乎将作品锁定,马平的灵感可能来自鸿祯塞的“暗道”,或者说来自充满虚无的黑暗和不断与黑暗斗争的徒劳,以及作者不被任何形式上的东西所征服获得的超越。
19世纪法国文学评论家莫里斯·布朗肖曾说,真正的写作是由外部控制的。外部是一种中立的体验,即主体的割舍。《塞影记》割舍了三层主体,或者说是三个主体的自我割舍成就了这部作品真正的写作。首先被割舍的主体是马平本人,大约是在写下“我”字开始,他就把自己割舍了。第二层被割舍的是一位作家,老祖宗雷高汉指定他撰写个人史。他是个东北人,打算来看油菜花却误入一幢玻璃房子。小说第三页提到《午夜之子》,书的主角萨里姆·西奈也是在临终前向其伴侣帕德玛讲述他的家族史。从这一层逻辑讲,作家是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所支配,被动进入了文学空间。在那里,异乡人的身份、立场和死亡的体验构成了写作的本源。从他提出“那么,汉子大爷,雷高汉,他是从哪一条路来到板桥湾的呢”这个问题,他也就把自己割舍了。作品的核心里,有一个孤儿雷高汉,他的一生被命运推攘前行,他的故事成为作家的作品,他自己也想用文字来铺一条小路,走到女儿面前去,但是“刚把大幕拉开,女儿就出来谢幕了。”因此,老祖宗雷高汉成为第三层割舍的主体。
经过这样层层割舍,写作主权层层让渡之后,《塞影记》就不再由作家构建,而成为它自身呈现出的文学景观。作家景三秋逗留在作品当中,在老祖宗的回忆里进进出出,跳跃撷取,他不仅拥有与武陵渔人相似的身份,还担任主要角色。他有来历,有立场,有情感的迷失,也有难以自揭的伤疤,通过与老祖宗相处获得了某种领悟和救赎。时间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折叠,以至于雷高汉时间、景三秋时间以及《塞影记》时间总共三层外部在一个文学空间里重叠,各种文化思想共存于这部作品中相互印证,并产生融合。仿佛是作品走出了“暗道”,并呈现出类似于布朗肖提倡的“文学共同体”的作品景观。可贵的是,作品并没有因为走出暗道而信马由缰(没有走向魔幻现实主义),反而愈发内敛纪实,保持着质朴的文化气质。
中西文化的比较和语言故事的承载
再说故事表达的文化。小说形式上的似曾相识和通俗易懂的故事,难免使人与美国畅销书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相提并论。盖茨比的故事发生在1919到1920年的十年间,雷高汉的故事也刚刚开始。同样是穷小子、社会边缘人,一个经历了美国社会的虚情寡义,看透黄金时代的流失;另一位在百年中国的恩山义海中度过一生,传达精神文明的赓续。两部作品形似而神非,主题与内涵截然不同,精彩程度不相上下。雷高汉的故事中,不时出现川剧《翠香记》《摘红梅》等选段,以及管火、踩假水等俚语,由于运用适宜,作品充满了巴蜀文化的水土气质。“无为”的思想、对“义”的践行和对“水”的信仰,也充斥着雷高汉的一生,这些都是中国传统道家文化的基础。故事保有这些水土气质也就保有了中华文明的根系和源头,因此这本书是一部扎扎实实的当代中国小说。
下一篇:没有了
